精选留学知识,分享海外经验
Connecting People for International Study
学长分享|我与寂寞丧偶房东的租房奇事
Jackson 2016-11-24
学长简介:李能,一切皆有可宁
生于80末,死于10086年。
专业:表面专业是建筑设计,真实专业是买卖人口
年龄:表面是18,实际上也是18
毕业院校:表面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实际上是李宁大学
我19岁的时候,在袋鼠国上学。
你知道的,很多国外大学的学生宿舍是很贵的,于是大部分留学生就要四处租房子。房子一般分为house(独栋洋房,有的新,有的破,住过最破的一个几乎只由木板搭成,走起路来咯吱响),unit(一般为小户型筒子楼,层高三到五层,没有电梯,但胜在简约质朴),apartment(通常配有门卫和电梯,室内健身房和游泳池,租金自然高)。
一般来说,这三种房型可以自由选择,有钱又懒,就选择apartment,可以选择房租里面包含每周账单,就不用操心别的什么了。而unit和house的房间差不多,house一般隔音效果不太高,但房子大,一般有后院,可以在里面种菜挖葱,适合大自然爱好者。而unit,价格通常居中,简易,有时候客厅会被房东隔起来,单独出租,如果你比较宅,只喜欢呆在房间里,人员结构相对简单、价格适中的unit,是不错的选择。
孔子讲究中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四合院总是镜面对称(不考虑入口的话),交通方正,正房居中,耳房在侧。所以我就先说说我住过三种户型里偏向中等的unit吧。
留学第一年,我住在一个离学校很远,处于当地小混混比较多的一片区域。有次夜晚回家,看见路边有一张沙发在燃烧。火光冲天,十分好看。那个温馨的两室一厅的unit,除了离学校稍微远些,周围小混混多些,客厅被改装成一个简易居室,让住户的活动空间少了些之外,十分宜居。在此我要多提一句,那个房间,铺的是原木地板。
木地板,这是一个重点,我建议朋友们在选择住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木地板,上面无遮盖物为好。请牢记。
关于这间unit的故事,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说说,我住过的另外一个unit,也是这篇故事的重点。
我21岁的时候,因为学业操劳,实在挤不出搭车上下学的时间,我便花高价,在学校图书馆对门处租了一个房间。
这同样是一个两室一厅的unit,在一片僻静但治安良好的小区之中(要知道很多区域都会有“爆菊街”的传说啊。让我高兴的是,这是房东自己买的房子,房东名为Richard,祖籍德国,在袋鼠国长住。Richard有个名为Max的上初中的正太儿子,这父子二人,住在大房间,小房间便租给了我,客厅则不住人,是我们的娱乐室。
这个房子比较温馨,看得出,不是为了出租而改造出来的。卧室、客厅、卫浴、洗衣间,都充满了人气。客厅朝北(袋鼠国讲究坐南朝北),干净明亮,可以抬头看见一大片天空。
和这一对外国父子生活,会觉得空间大一些,有意思些。比如Richard的职业为飞行员,经常要出差个三五天,这时候,我便和Max两人独霸整个房子。Max爸爸走后,他便形同疯狂,每天除了打电脑游戏,就是打电视游戏。托了Max的福,我的League of Legends技能飙升,已经熟练掌握了好几套购买装备的流程。
而孩他爸在的时候,我们也会老实些,有时候我帮着Max辅导数学,他上中学,再过几年就要考大学了,有时候,他会请教我关于数学公式里如果括号里是加减括号外是乘除应该先算哪个部分的问题。Max看我经常做模型,便励志也要上建筑设计专业。我心里呵呵一声,便对他说那你的物理还得好好学。可惜我光笑Max数学差,没想自己的口语也不怎么好,把Physics 说成了 Physical,于是Max接下来便开始刻苦为了上大学锻炼身体。
我从来没见过Max的母亲,倒是看见Richard偶尔会把漂亮的空姐带回家里,当着我的面一番缠绵,而Max往往见怪不怪,继续看他的宠物小精灵。
日子在上学的紧迫和回家的悠哉中切换,适应了,就觉得倒也充实。
有天回家,看见父子俩迎在门口,以为有什么大事件,结果两人告诉我,这天是爱护地球日,我们要响应号召,在即将到来的八点,关灯一小时。
德国人的严谨确实是出了名的,八点一到,脸上布满了前所未有的庄严与隆重的Richard,便迅速关掉了房间里的所有灯。甚至连我的电脑和手机也逼着关掉了。大哥啊,这些明明不用通电源的啊。
无论如何,家里的设备全关了,都有些电子产品依赖症的我们便无所事事起来。夜晚,安静,关了灯后,只有窗外稀疏的光漏进来,地面上铺着哑光的毛毯,几乎没有反光。我们聊了会天,打了会牌,墙上的钟表才过去二十分钟。百无聊赖之下,我便建议大家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嗯,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中二也比较晚,现在想想不知道这破游戏三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好玩的。
这对外国父子好像大概了解怎么玩,便陪着我玩了会。我们玩加州扑克,不能退出,输了的人便接受惩罚。
嗯,我牌技也非常之一般,输了好几次。
于是我喝过了一次马桶里的水(Max的主意),在脸上贴纸条(他爸的主意,明显善良多了),又干了些七七八八的无聊事之后,便要求接下来大家开始说真心话。
结果接下来又是我输,Max便问我破处是啥时候。我当然不能说我还没破过啊,便和他说是在十八岁。Max撇撇嘴,说比他晚多了。
总之,在被这对父子羞辱了一阵子之后,我似乎苦尽甘来,开始转运,频频赢牌。可毕竟人家是房东,我也不好赶尽杀绝,便以问问题为主。
问了一会,看这对父子似乎也没什么避讳和禁忌,我脑袋一抽,便问了一个说出来就有些后悔的问题。我当时问Max,你妈妈去哪了。
当时说完这个问题,在黑暗里,我隐约看到了Max脸上复杂矛盾的表情。妈妈在我身边啊。she’s here with me,Max当时这么答到。
那时候我才知道,或许Max的母亲已经告别人间了,所以他才会说出妈妈在身边这样的话,以安慰自己。我顿时又对这乐观的父子俩生出了更多的好感来。
那晚,我们玩到了夜深,到后来连熄灯一小时这事情也忘了,一个小时后,窗外的灯光多起来、亮起来,我们便借着外面的亮光,继续玩闹。
很多年以后我还是记得在异国他乡那晚的欢快时光,我们打着牌,星光抑或是月光,就那么轻轻淡淡地钻进窗户。
那天之后,我感到自己和Max的关系又更好了些。他谈起他的妈妈的时候也多起来,有时候,他说起和妈妈吃寿司的事情,尽管我知道那间寿司店是最近才开的,可我只当是Max怀念母亲,便幻想着她还陪着他。于是我只得转换话题,拉着Max去打游戏。
到后来有一天吧,Richard要连续出飞行任务一周,便吩咐我看好Max,别让他调皮。我和Max互看一眼,暗自一笑,等Richard走后,房间便又成为了我们的天堂。
开始的几晚我们就睡在客厅,后来有一晚,变天了,风幽幽地刮,我便让Max回房间休息。我看着Max心不甘、情不愿回房间的样子,有些不忍,便提出和他一起睡,借此陪陪他。这哥们倒是不领情,觉得两个大男人睡一起,太别扭。
没办法,我便回了房间。那晚,不知是不是吹多了风,我睡得并不踏实,深夜里,半梦半醒间,我听到房间外隐隐有异响。
我拖着身体,打开一道门缝,往外看。
客厅里,有个身影,弯着腰,在找着什么。这晚乌云翻滚,窗外光线黯淡,但我依然认出来,那正是max。不是小偷啊,我放下心,便又睡了过去。
可过了一会,我感觉我的房门,被推开了。
那个并不比我矮小的、毛烘烘的,一团黑影子,推开我的门,先是探进半个身子,看我没有反应,便走了进来。难道Max是在梦游?我原地躺着,想看看他要干什么,便没有发出动静。我看见,Max悄悄地,走到我房间的一处拐角,沿着地毯和墙壁的交界处,用手把地毯掀了起来,似乎是取出了什么东西,铺好地毯,便离开了。
他离开了,我便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身体起来,看见Max已经给我们做好了早饭。这哥们,倒是一直很健康。边吃着东西,我边问Max,昨晚睡得如何。Max说他睡得很好。我对前晚Max的举动有所好奇,可他完全不提,我自然也不好多问。我只记得,那天吃完饭,Max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到,生,你知道吧,我爸爸不在的时候,我妈妈,会陪着我入睡呢。
看着Max单纯、魅惑又明亮的眼神,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病得更重,一阵阵地发冷。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再半夜醒过来了,我不问,Max便也不再过多谈起他的母亲,但他似乎也并不孤单,有时Richard出远门,我在学校通宵作业,他倒也并没表现出有多孤单。
到了那年的暑假,我打算回国了。和这两父子一起居住的一年,舒服,自在,彼此都生出了深深的感情。临走那天,趁着父子不在,我打算来个大扫除,以示报答。
当然主要也是我的房间,太他妈脏了。
在文章的最前面,我说过,房间里最好是木地板,而Richard他们的房间,几乎都铺着柔软的毛地毯。这地毯,打扫起来太难了。
我举着笨重的吸尘器,围着地毯吸了个遍,浑身出汗,但还是觉得不干净。尤其是地毯边缘处,一些灰尘和皮屑,几乎都被吹起来,又落进了地毯和地板间的夹缝里。
我突然想起来曾经有一晚,Max梦游来我房间,还迷糊糊地把地毯的一角掀开了。于是我走过去,把地毯掀起来,准备清洁一番。
我看见,地毯下面,有一片薄薄的膜。如果仔细看,那膜,像一张皮。
皮上面还有清晰可见的毛孔和皱纹,如果看得更仔细些,就能分辨出,那是一张脸皮,上面有一处空洞,是原先眼睛在的位置。
那是一张边缘被什么利刃切割开的、并不完整的、像一块拼图一般的脸皮。
那天我最终只清洁了我的房间,而客厅、其他房间的地毯,我并没有再翻动过。那之后,我便彻底告别了这对父子,因为要省钱,便搬到了其他便宜地方。
因为学业忙碌,我很少有功夫想起这对曾经交过心的父子了。只是有时候在孤枕难眠的夜晚突然惊醒,我会下意识地看向枕头一旁,幻想着在不知名的什么地方,有一个男孩,他的枕边,有一张被切割成碎片又被拼补起来的脸,正温柔含情地注视着他。
↓↓下载APP,马上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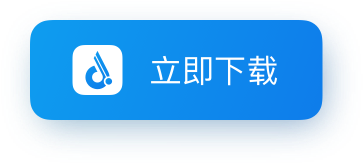
输入国家名,获取详细留学资料!
留学资讯再也不用东搜西找啦~
推荐阅读